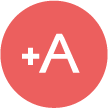我的读书五部曲
本文字数: 1818
小时候我住在陕西乡下,买书要去七八公里外的镇上,能买到的主要是《儿童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《童话大王》和《故事会》等期刊。每次母亲去镇上,我都要软磨硬泡地缠着母亲,让她给我几块钱,买一两本看。书一到手,我就迫不及待地翻开,先看印着美丽图案的封面封底,再看目录,从中挑选最喜欢的篇章看,最后逐字逐句地把整本书看完,连广告也不放过。那些广告对我也充满魅力,常常是某某书又结集出版了,主要是什么内容等。我常常看了又看,然后怯生生地拿着那广告去找父亲,看能不能给我一点钱,邮购一本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父亲驳回,理由就是:“这是课外书,看这些书是不务正业,你应该好好学习学校发的课本。”
这种对书的饥渴一直持续到我中专毕业在陕西韩城上班之后。那时单位附近有一家图书馆,古香古色、白墙灰瓦、飞檐翘角,里面装满了书。有些书已经旧了,年代久远,但仍遮掩不住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智慧光芒。印象最深刻的,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,书名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,只记得当时看完这本书时,感受到深深震撼。我此前所看的大多是《少年文艺》《青年文摘》之类的期刊,讲的大多是个体的故事和感受,但这本关于历史的书,从宏观视野反观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,提出了一些我之前没有听说过的观点,犹如醍醐灌顶,照亮了我蒙昧的心。如果要说有启蒙,这大概就是我的启蒙吧,虽然来得有点晚。我带着强烈的求知欲,一本接一本地,几乎读完了这个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。同事们常常笑着问我:“是不是已经学富五车了?”
再一次的大批量阅读,发生在我备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。当时备考的科目中,有一门是《古代汉语》,里面经常引用《尔雅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《史记》中的句子来剖析,而我能看得懂的没几句。那时我借住在西安交大附近,距离陕西省图书馆很近。我常常从书中查到所引用句子的出处,把书名抄到本子上,然后搭公交车到省图书馆,一本一本地把书借回来,再一句一句地查找句子在原文中的意思。常常为了理解透一个句子的意思,需要看完整篇文章,《尚书》《尔雅》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史记》等就这样闯入了我的视野。我囫囵吞枣地吞下去,虽然不太理解一些文章的精髓,但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脉络有了一个大体的掌握,也奠定了相对坚实的文字基础。那时读过的书中,最纵横捭阖的是《尚书》,最荡气回肠的是《史记》,最让人心有戚戚的是《伯牙绝弦》,最心生向往的是《兰亭集序》。
读研期间,我读书从先前的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分析。课堂上需要围绕一个个文本,结合历史、社会等种种因素,对文本进行剖析。当书成了不得不读的东西,成了每堂课必须研究、分析的东西时,我突然发现,读书不再像青少年时期那样,让我感到现实生活之外的丰富世界和乐趣。相反,读书变成了苦差事,变成了一种压迫,一种不得不完成的任务。我常常把书从图书馆一摞摞地借回来,快到期时,又一摞摞原封不动地还回去。这一时期书虽读得艰难,但文本剖析培养了一种理性分析的能力,使前期的阅读积累有所升华。我写的文章《那一场为梦想而奋斗的往事》首次在《中国名校硕士谈考研丛书——风雨考研路》上刊登,关于电影《紫色》的评论《女人是什么》有幸在《看电影》杂志上发表。这既让我感到振奋,也激起了我对未来读书和写作方向的重新定位与思考。
成为一名公务员后,随着生活阅历和年龄的变化,我读书变得驳杂。我喜欢读《万历十五年》《中国哲学史》,想从中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,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密码;喜欢读人物传记,如《为什么是毛泽东》,从字里行间发现伟大人物成功的秘密;喜欢读《瓦尔登湖》《休息不可耻》等一类的散文,在工作累了的时候,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滋养;喜欢读谈行医、做菜的文章,发现行医与做菜万道归一,好医术与好菜的基础都是顺应天时。
高尔基说,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。对我来说,书籍不仅仅是阶梯,更是导师、伙伴和助手。在我迷茫徘徊时,是书为我指引了人生方向,使我看到了“别样的生活”,从而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;在我需要提升时,是书使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,总结经验、汲取智慧,发现了人生的无限可能性;在我孤独焦虑时,还是书帮我打开了视野,让我的思想纵横四海、驰骋古今,感受到生命的广阔无垠。
这种对书的饥渴一直持续到我中专毕业在陕西韩城上班之后。那时单位附近有一家图书馆,古香古色、白墙灰瓦、飞檐翘角,里面装满了书。有些书已经旧了,年代久远,但仍遮掩不住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智慧光芒。印象最深刻的,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,书名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,只记得当时看完这本书时,感受到深深震撼。我此前所看的大多是《少年文艺》《青年文摘》之类的期刊,讲的大多是个体的故事和感受,但这本关于历史的书,从宏观视野反观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,提出了一些我之前没有听说过的观点,犹如醍醐灌顶,照亮了我蒙昧的心。如果要说有启蒙,这大概就是我的启蒙吧,虽然来得有点晚。我带着强烈的求知欲,一本接一本地,几乎读完了这个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。同事们常常笑着问我:“是不是已经学富五车了?”
再一次的大批量阅读,发生在我备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。当时备考的科目中,有一门是《古代汉语》,里面经常引用《尔雅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《史记》中的句子来剖析,而我能看得懂的没几句。那时我借住在西安交大附近,距离陕西省图书馆很近。我常常从书中查到所引用句子的出处,把书名抄到本子上,然后搭公交车到省图书馆,一本一本地把书借回来,再一句一句地查找句子在原文中的意思。常常为了理解透一个句子的意思,需要看完整篇文章,《尚书》《尔雅》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史记》等就这样闯入了我的视野。我囫囵吞枣地吞下去,虽然不太理解一些文章的精髓,但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脉络有了一个大体的掌握,也奠定了相对坚实的文字基础。那时读过的书中,最纵横捭阖的是《尚书》,最荡气回肠的是《史记》,最让人心有戚戚的是《伯牙绝弦》,最心生向往的是《兰亭集序》。
读研期间,我读书从先前的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分析。课堂上需要围绕一个个文本,结合历史、社会等种种因素,对文本进行剖析。当书成了不得不读的东西,成了每堂课必须研究、分析的东西时,我突然发现,读书不再像青少年时期那样,让我感到现实生活之外的丰富世界和乐趣。相反,读书变成了苦差事,变成了一种压迫,一种不得不完成的任务。我常常把书从图书馆一摞摞地借回来,快到期时,又一摞摞原封不动地还回去。这一时期书虽读得艰难,但文本剖析培养了一种理性分析的能力,使前期的阅读积累有所升华。我写的文章《那一场为梦想而奋斗的往事》首次在《中国名校硕士谈考研丛书——风雨考研路》上刊登,关于电影《紫色》的评论《女人是什么》有幸在《看电影》杂志上发表。这既让我感到振奋,也激起了我对未来读书和写作方向的重新定位与思考。
成为一名公务员后,随着生活阅历和年龄的变化,我读书变得驳杂。我喜欢读《万历十五年》《中国哲学史》,想从中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,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密码;喜欢读人物传记,如《为什么是毛泽东》,从字里行间发现伟大人物成功的秘密;喜欢读《瓦尔登湖》《休息不可耻》等一类的散文,在工作累了的时候,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滋养;喜欢读谈行医、做菜的文章,发现行医与做菜万道归一,好医术与好菜的基础都是顺应天时。
高尔基说,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。对我来说,书籍不仅仅是阶梯,更是导师、伙伴和助手。在我迷茫徘徊时,是书为我指引了人生方向,使我看到了“别样的生活”,从而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;在我需要提升时,是书使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,总结经验、汲取智慧,发现了人生的无限可能性;在我孤独焦虑时,还是书帮我打开了视野,让我的思想纵横四海、驰骋古今,感受到生命的广阔无垠。
□海南省三亚市市场监管局 康燕玲